在湖南的歲月里,她留下“堅忍韌性的笑”
——紀念林徽因誕辰120周年

林徽因畢業照。(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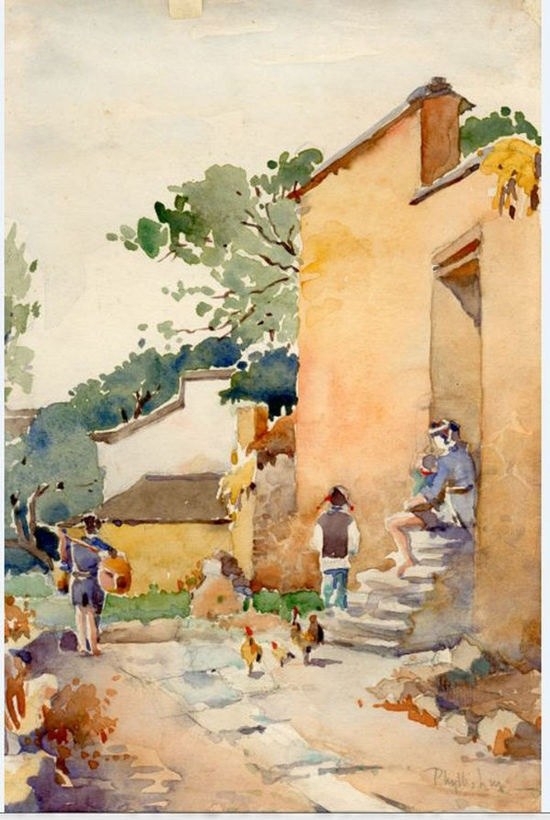
林徽因水彩畫《故鄉》。
湘江
當地時間5月18日(北京時間5月19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正式向林徽因(1904年-1955年)頒發遲到近百年的建筑學學士學位證書。林徽因曾以優異成績修完建筑課,與當時的梁思成不分伯仲。“當年沒有授予她學位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女性身份,而這個錯誤如今需要被糾正。”該校設計學院院長弗里茨·斯坦納(FritzSteiner)說。
作為中國現代建筑先驅、詩人、作家,林徽因不僅留下了天然去雕飾的散文、詩篇,更一生致力于中國古建筑的考察、研究和保護工作,為研究中國傳統營造學的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貢獻了諸多力量,參與建立了中國傳統木構建筑的研究系統。她以詩人的敏感與才情,率先提出了極富人文美學意味的概念——“建筑意”。
她不長的一生,光華熠熠。但她的人生并非時時歲月靜好,而是在國難、疾病、貧困和時代變遷中掙扎著、不懈地追求“美”之理想。湖南大地記錄過她的行跡。1937年10月,抗日戰爭烽火連天,林徽因與梁思成攜全家寓居長沙,隨之經湘西的沅陵、晃縣(今屬新晃侗族自治縣),南遷至西南聯合大學所在的云南昆明。在1939年,她記述戰時歲月,寫下散文《彼此》:“經過炮火或流浪的洗禮,變換又變換的日月,難道彼此臉上沒有一點記載這經驗的痕跡?”“口邊那酸甜的紋路是實際哀樂所刻劃而成,是一種堅忍韌性的笑,因為生活既不是簡單的火焰時,它本身是很沉重,需要韌性地支持,需要產生這韌性支持的力量。”
2024年6月10日,是林徽因誕辰120周年。回望她在湖南的時光,那“堅忍韌性的笑”,每每浮現眼前。
長沙:
在空襲中僥幸逃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那時,梁思成、林徽因一行還在山西五臺山考察古建筑。他們發現了唐代木構建筑——佛光寺大殿,為保存完好的建筑、塑像、壁畫和唐人墨書題記激動萬分。等出了山,到了有報紙的地方,他們才知道盧溝橋事變已過去五日了,急忙啟程回北平。路上,林徽因寫信給女兒:“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頂有決心方好。”
1937年7月底,北平淪陷,營造學社被迫暫時解散。不久,梁思成接到日本“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梁林夫婦決意攜全家,和清華、北大的教授們一起離開北平,去往“自己的后方”。含淚離開北平前,林徽因做了一次身體檢查,醫生警告已有肺病的她不可疲勞奔波。“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
9月4日晚,林徽因夫婦連夜收拾行裝趕往天津與家人會合。月底,他們攜年僅八歲的再冰和五歲的從誡,帶上林母,一路西行南下。由于戰火,交通受阻,他們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到達長沙時,已是1937年10月初。
初到長沙,一家五口先是借住在韭菜園教廠坪的一處民宅,后又遷至圣經學院的三間簡陋小屋。不過,當時南遷的還有聞一多、朱自清、楊振聲、金岳霖等朋友們。林徽因性格爽朗,依舊如在北平一般,熱愛組織聚會“苦中作樂”:“對于過去有許多笑話和嘆息,但總的來說我們的情緒還很高。”
但戰爭催趕著他們的腳步。1937年11月24日,長沙遭遇敵機空襲。林徽因記錄下驚心動魄的一幕:“沒人知道我們怎么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里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斬斬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的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沖出旁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
12月8日清晨,林徽因一家告別長沙,開始向陌生的西南遷徙。他們預計,“要搭汽車走十天艱難的旅程到云南去。”
沅陵:
古城可愛極了
次日,他們乘汽車經常德、桃源、官山抵達沅陵。
這一路,山錯落,水清澈,秀美的風景讓愛美者快樂。林徽因不禁想起了好友沈從文的小說《邊城》:“有時頗疑心有‘翠翠’這種人物在!”
她給沈從文寫信:“今天中午到了沅陵,晚上住在官莊的,沿途景物又秀麗又雄壯時就使我們想到你二哥對這些蒼翠的,天排布的深淺山頭,碧綠的水和期間稍稍帶點天真的人為的點綴,如何的親切愛好,感到一種愉快。天氣是好到不能更好,我說如果不是在這戰期中時時負著一種悲傷哀愁的話,這旅行真是不知幾世修來的。”
沅陵古稱辰州,是一座州府級的城池,擁有8處門樓,綠水繞洲,街巷密集,水陸交通繁忙。
踏上沈從文“一提及它時充滿了感情的辰州地方。”林徽因夫婦即拜訪了沈從文與大哥沈云麓共同建造的、位于天寧山頂的“蕓廬”。在這棟別致有雅趣的小樓里,他們還意外見到了沈從文的弟弟沈荃。他們與沈家兄弟在樓上廊子上坐著,望著碧綠的山和水聊天。這難得的休閑時光,撫慰了顛沛流離中的哀愁。
林徽因致信沈從文:“沅陵的風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們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記憶,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無論什么時候,最好當然是打完仗!說到打仗你別過于悲觀,我們還許要吃苦,可是我們不能不爭到一種翻身的地步。”
在沅陵,他們只小住了三日。
晃縣:
一次相遇,與八次別離
晃縣在舞水的“幾”字形彎中間。當12月上旬,林徽因一家抵達這座偏僻的湘西小城時,這里的旅店已經住滿了西遷難民。當時,由于中央航校西遷昆明,從沅陵開往貴州貴陽的客車都被派去轉運學院了。在湖南寒冷潮濕的冬天,林徽因在路上患上了急性氣管炎,又迅速轉為急性肺炎,一直發著高燒。
多年后,梁從誡還對初抵晃縣的那個雨雪霏霏的夜晚記憶猶新:“為了投宿,父母抱著我們姐弟,攙著外婆,沿街探問旅店。走完了幾條街巷,也沒能找到一個床位。就在那走投無路的時刻,竟發生了一個‘奇跡’:從雨夜中傳來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令人頗有‘如聽仙樂耳暫明’之感。誰會在這邊城僻地奏出這么動人的音樂?父親想: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許能找他幫一點忙?他闖進了漆黑的雨地,‘循聲暗問彈者誰’,貿然地敲開了傳出琴聲的客棧房門。樂曲戛然而止。父親驚訝地發現,自己面對的,竟然是一群身著空軍學員制服的年輕人,十來雙疑問的眼睛正望著他。父親難為情地作了自我介紹并說明來意。青年們卻出乎意料地熱心,立即騰出一個房間,并幫忙把母親攙上那軋軋作響的小樓。”
在這家旅社拉琴的,正是中央航校的學員,一行共8人。在晃縣停留的日子里,梁林夫婦與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將他們視為弟弟。
在晃縣,一位同樣在等車的女醫生為林徽因開了藥方,林徽因的病漸漸有所起色。在旅社用薄板隔出的小屋內躺了兩周后,林徽因一家登上一輛破舊硬擠的公共汽車,再次踏上艱辛的西行之路,并于1938年1月,經貴州抵達昆明。
這次重病,給林徽因的身體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但令她欣喜的是,在昆明,她又見到了那8個飛行員弟弟。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他們有時還一起去郊游、游泳、唱歌、拉琴。一年之后,當他們從學校畢業時,由于沒有親屬在昆明,便邀請梁林夫婦作為他們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并致辭。
抗戰時,中國空軍處于嚴重劣勢,那時流傳一種說法:空軍飛行員從航校畢業到戰死,平均只有六個月。從中央航空學校的校訓中可見一斑——“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于盡!”按照慣例,每個飛行員出征前都要留下親人的聯系地址,戰時通信不便,他們8人就留下了林徽因家的地址。
1939年開始,林徽因陸續收到部隊寄來的陣亡通知書,以及他們的日記本、鋼筆、照片等私人遺物。每次接到遺物,林徽因都泣不成聲,心被一次次“炸成了窟窿”。1941年3月,林徽因23歲的三弟林恒在對日成都空戰中,也血灑長空。1944年3月,她在晃縣結識的最后一位飛行員弟弟林耀,犧牲在衡陽會戰中。
懷揣著“中國的悲愴”,這位描繪過柔軟的“人間四月天”的知識分子發出了沉郁的聲響:“中國還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抗戰會勝利,中國建筑研究事業會繼續。她始終沒有過一絲彷徨。

Copyright © 2017 m.haoxunlei.com 湖南政研網 湘ICP備18001534號 版權所有
主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承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辦公室、政策研究事務中心 技術支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