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一“夫子”
——禮學家陳戍國先生其人其事

陳戍國。 陳冠偉 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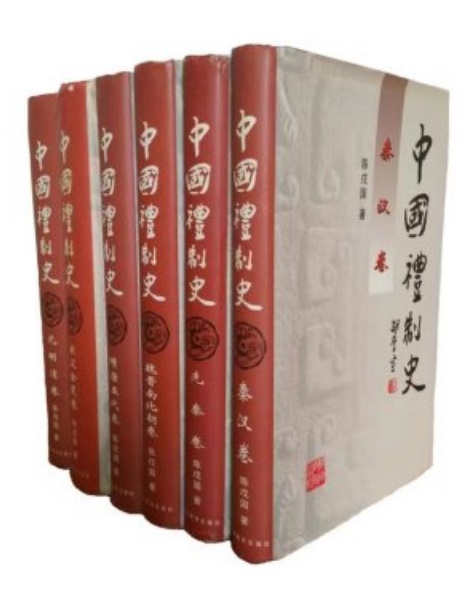
陳戍國代表著作《中國禮制史》。

1994年陳戍國與妻子盧蓮香在湖南師范大學。 謝鴻鶴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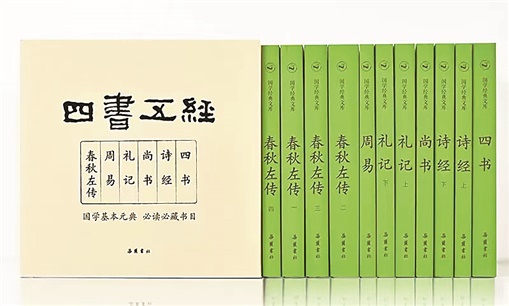
《四書五經》陳戍國導讀校注本。
編者按
中國自古以來有禮義之邦美譽,禮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作為我國經學、禮學研究界改革開放以后成長起來的著名學者,著名禮學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陳戍國教授在相關領域辛勤耕耘,奮力治學,在中國古代禮制史研究、儒家經典整理研究等方面著述甚豐,具有開拓性貢獻。2023年1月7日,陳戍國教授因病逝世,享年77歲。《湘江周刊》特邀陳戍國教授博士生弟子彭永撰文懷念。
彭永
泰山其頹,哲人其萎。先生遽歸道山之后,臺灣成功大學教授柯金虎發唁電稱“世上少了一個讀書人的楷模”。斯人已逝,斯文長存,我們恍惚中似乎又見到這位特立獨行的“夫子”:一頭白發,右手扶著鏡框,微微傾斜著身子,在陽光里、綠葉下自豪開心地笑著,那些苦難、那些遭遇、那些嘲諷都已遠遠被他甩在身后。
戴了十八年的“帽子”
湖南隆回,“睜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鄉。1946年,陳戍國先生出生于隆回灘頭鎮柏水村,父親是一名鄉村教師。陳戍國記憶力超群,又肯下苦功夫,從小學到高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成為當地父母教育子女刻苦讀書的楷模。
1961年,陳戍國考入隆回一中,書生意氣,有一次指出老師的錯誤,老師惱羞成怒,結果被整了材料,“該生不宜錄取”進了檔案。語文老師易重廉向學校建議:該生出身貧下中農,年紀尚小,要考慮學生前途;況且該生成績優異,大學如不錄取,也會影響學校的升學率。學校采納了易老師的建議,“該生不宜錄取”的鑒定沒有進入檔案。
1964年7月,經歷報考風波的陳戍國考入湖南師范學院中文系。之所以填報這里,一是因為不僅不收學費,還有不等的生活費補貼;二是自1953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后,湖南所有學校文科的本科,都集中在這里,除了師范學院,就沒有文科本科可考了。
在湖南師范學院求學期間,陳戍國深得辭賦名家馬積高等先生的賞識。但是,為人正直、愛發議論的脾性,又讓他摔了大跟頭。他對特殊時期的時局發表了看法,被同學告發,被打成“反動學生”,先是俟罪長沙、挨批被斗,后下放到汨羅江畔,與馬積高老先生等一同勞動改造。
大學延遲兩年畢業后,陳戍國先是被分配岳陽某農場,后發配回原籍隆回。隆回縣文教局又將其發配到“隆回的西藏——小沙江”,要他負責從縣城挑書本紙張去小沙江,單程就有200多里遠。經過一年多的勞動鍛煉后,陳戍國被安排到隆回十二中,再調整到巖口中學教高中。從巖口中學到老家柏水有40余里路,當時有班車,也有拖拉機,但陳戍國總是走路回家。身背黃色挎包,腳穿輪胎做的皮草鞋,是他不變的形象。
1979年,研究生招生考試恢復,得知消息后陳戍國決定報考。他第一志愿報考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專業,雖說總分超過錄取線,但由于“反革命”的帽子沒有摘掉,不予錄取,最后轉到第二志愿西北師范大學,被同樣“挨過批斗”的郭晉稀教授收到門下。
1984年,戴了18年“反革命”帽子的陳戍國終于被平反。此時他在岳麓書社擔任編輯,時值盛年,醉心學問,白天編輯書稿,晚上鉆研學問。他不修邊幅,長年穿著一套墨綠色的衣裝,低頭走路不抬頭看人,幾次被門衛當成郵遞員拒之門外,鬧出笑話。
1987年,年已不惑的他考入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當今研治《禮儀》第一人”(顧頡剛語)沈文倬先生。他1989年畢業后輾轉任職于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師范大學、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陳戍國一生清貧,在西北師范大學讀研究生與在杭州大學讀博士的時候經歷了一段非常艱難的生活,艱難到寒假乏資無法與家人團聚,艱難到數九寒冬還在外打零工維持生計。這種艱難處境下,又有幾人能夠堅持向學而不改其心志?
“曾經碰到過所謂‘教育家’玩弄權術、故意制造的橫逆,也曾經遭到金錢的困擾。對付那些橫逆與困擾,我也只能像抹去蜘蛛網一樣置之不顧。”正如他在《中國禮制史》后記所言,處“橫逆與困擾”之境,研治古禮,怡然自樂,不覺時光之流逝,此即做學問之境界乎!
板凳一坐十五年冷
苦學,是陳戍國的標識。他在柏水小學就讀時,放學回家,上山砍柴,遇見松油成坨就撿,以備晚上學習點亮之用。雖然睡前洗了臉,但翌日的臉色堪比包青天,實在比鑿壁偷光還寒酸。
在省博物館工作期間,陳戍國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治學,保衛科反映其辦公室燈光經常亮到凌晨3、4時,有時乃至通宵達旦。同事擔心他身體吃不消,向他請教熬夜不累秘笈并表達關心。他說以冷水洗頭,并說自己在辦公室坐久了也會鍛煉,做自編體操、舉凳子等。宿舍和辦公室有一里之距,上下班會口含一口清水步行,以免在馬路邊行走吸收不清新空氣。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陳戍國說,能讓他靜心做學問,就是一件再幸福不過的事了。在撰寫《中國禮制史》的15年里,他讀過的各種專著達600多部。
不過,這套專著推出前學界對陳戍國并不怎么關注,更談不上鮮花和掌聲,熟悉的人甚至認為他多多少少有點“怪”:單位組織公費旅游,他一次都不去;不愿意裝電話,不買手機,不喜歡與人閑談應酬;連續幾年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也沒有承擔過一次課題,崗位津貼申報的是教授中的最低檔。他腦子里頭可能就只有讀書這個事,這使得他無暇顧及其他,不愿與人虛與委蛇,自然就被一些人認為性格上有些瑕疵。
陳戍國堅信做學問沒有捷徑,唯有下苦功夫。讀研時他向武漢大學黃焯先生請教學問,多有書信往還,黃焯先生曾贊其“當今治學問若陳君者,實乃鳳毛麟角。”他下苦功夫的精神,從學外語即可窺見一斑。中學、大學學了俄語和英語,讀碩士時學了日文,讀博士時又學了德文,不過他的外語只能讀寫不會說聽,第一次考博時考的是北京大學,專業成績第一,但北大博士要面試口語,陳戍國只進去了不到一分鐘,就搖著頭出來了,未能如愿。
陳戍國惜時如金,從不參與無謂的交往和閑聊。他在隆回十二中的宿舍門上貼了張紙片,工整地寫上“謝絕閑聊”。在宿舍的墻上貼上胡適的四句話:“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認真地做事,嚴肅地做人。”他備課充分,教案寫得認真,但課堂上從不看教案。示范朗讀課文有板有眼、一字不茍,恨不得把文字里蘊藏的意義都給宣泄出來。他的板書清癯削瘦,十分工整,撇捺拖得細長。
同在岳麓書院的張松輝教授是《道德經》研究名家,多次建議陳戍國爬山鍛煉身體,他說沒必要,因為他自編了一套健身操,每當自己在屋里讀書累了,就在室內踢踢腿,彎彎腰,效果也不錯。張松輝想到《莊子》里的一段話:“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高山密林之所以能夠給一個人帶來愉快,是因為這個人的精神生活還不夠豐富,所以還需要外物來為自己添加一些樂子。那些思想境界高的人,精神生活特別豐富的人,他們不需要山林,不需要外物。陳戍國大概就是這樣。
陳戍國對善本書尤其寵愛有加。當年兒子冠偉尚幼,一家六口僅靠他一人拿著微薄工資養活,缺吃少穿,生活舉步維艱,一分錢掰成兩半用,平時出門辦事,連公交車都舍不得坐,衣服洗爛洗白了也舍不得丟,哪有余錢去買書。但當他看到書店新到的善本書時,腳就如注鉛一樣難以移動。謝鴻鶴是陳戍國教過的高中生,有一個場景他記得特別深刻。有一次,他陪著陳戍國從省博物館挑著兩個籮筐走到袁家嶺新華書店,買完書后,扁擔兩頭一頭籮筐坐著兒子冠偉,一頭籮筐裝著新買的書,再從袁家嶺走回省博物館。回家的路上,挑著書和兒子的陳戍國像一個打了勝仗凱旋的將軍,洋洋得意,健步前行,幸福感爆棚地說:“書是寶貝,兒子更是寶貝,都是寶貝,都是寶貝喲!”
“我讀大學的時候,帶著‘鐐銬’攀登,并未自甘沉淪。后來不戴‘帽子’了,我亦未貪圖安逸,仍然刻苦求學。不敢說學有所成,但我感覺到活得充實,一年比一年充實。沒有百折不撓的意志,不能吃苦,治學也難。”幾十年之后,在一封寫給大學生的信中,陳戍國這樣回顧自己的求學經歷。
填補了我國人文學科的重要空白
陳戍國的學術傳承有兩個源頭,一個是西北師范大學的郭君重晉稀先生,另一個則是杭州大學的沈鳳笙文倬先生。郭先生學術傳承為湖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楊遇夫樹達先生、曾星笠運乾先生,是曾、楊二位先生看重的親炙弟子與高足。郭先生是古典文學、古代文論、音韻學大家,陳戍國從郭先生學詩,郭先生指示從禮入詩,因此,《詩經芻議》是以禮說詩的學術巨作,在以禮說詩方面做出了學術貢獻,陳戍國先生是郭君重晉稀先生的學術衣缽傳承人,是曾、楊二師的再傳弟子。
沈鳳笙文倬先生的老師是曹谷孫元弼先生(著《禮經學》七卷、《孝經學》七卷、《周易學》),曹元弼先生的老師是黃元同以周先生(著《禮書通故》),黃、曹兩位先生皆曾為翰林院編修,為清代大學者、禮學名家。陳戍國是黃先生的三傳弟子,是沈先生的學術傳人。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院長陳仁仁教授認為,陳戍國的學問其實是“四部之學”,并不僅僅是在禮學方面。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禮制禮學,其次為中國古代文學,旁及中國古代史學、古代文獻學。陳戍國重視著述,先后出版《中國禮制史》《中國禮文學史》《詩經芻議》《十子平議》等學術專著多部、《四書五經校注》等古籍整理成果多種。其中,《中國禮制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禮制通史,凡六卷,280萬字,構筑了當代禮學、禮制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術高峰,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這一重要領域的光輝熠熠閃爍,填補了學術界空白。著名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清華大學李學勤先生認為,“這是我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學術著作出版上的一樁盛舉。”著名古文字學家、古文獻學家裘錫圭先生評價道,“此書是我國第一部禮制研究通史,填補了我國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空白。”《中國禮文學史》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禮文學史,第一次提出“禮文學”的概念,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他以一人之力標點注釋四書五經,既集思廣益、融會貫通,又獨立思考、推陳出新,最后落實到確詁,時有一些超乎前修時賢的創見,代表著當今學者治經的最新成果。
“明知力有未逮,偏要迎難而上,實在是因為對于數千年禮義之邦迄今無禮制通史之局面心有未安。不賢者識其小者,初衷如此,豈止‘為之小’亦屬不易也。”正是因為這種擔當,陳戍國用著述的方式呈現書生報國的情懷。
“讀書著書滋味長”
“不要太過于追求個人名利,還是淡泊明志、任其自然為好。對社會的貢獻,有益于文明的成果,才是最重要的。我認為能生活下去就行,與那些所剩者唯有金錢的男女‘大款’相比,還是讀書著書滋味長。發明原子沖擊器的著名科學家勞倫斯說得好,與其花那么多時間申請什么專利,還不如抓緊時間多沖擊幾種原子呢。個人聲名,自有公論,亦何必花時間討個什么說法呢(當然原則問題不在此列)。”這是陳戍國寫給當代大學生一封信中的話。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2004年,學校動員他申報湖南省第七屆社科成果獎,他拒絕得很干脆。學校考慮人文社科學科建設和發展之亟需,設法反復動員后依然無果,只得請他的學生和書院老師出來幫忙,填寫材料,方得以申報上去。最后,獲得唯一的一等獎。2012年,學校動員他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陳先生拒絕,學校反復動員并請其他老師和學生協助,陳先生也慮及學校和書院發展之需申報了,第一年“重大”沒成,拿了個“重點”,第二年繼續,取得了成功。
為什么不愿意參加很多人趨之若鶩的評選?在他的一本著作的后記里,有這樣一段話:
“迄今為止,陳戍國手里沒有一張關于著作或論文獲獎的證書。但從來不看重學術論著獲獎與否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本人相信什么獎也不可能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唯有努力學習才能與時俱進,當然也相信學術界自有公論。陳戍國注意過那些獲獎的論著,認為其中好的固然不少,可笑的東西也多。感謝那些在學術界主持正義的專家朋友。”
陳戍國的兒子陳冠偉珍藏著父親49歲生日時寫的一首詩,那時他剛搬到湖南大學,或許這是陳戍國先生人生的濃縮:
登山望水思緒飛,四十九年是與非。
風雨饑寒常困我,瘴霾荊棘老纏誰?
東南西北留名跡,甲乙丙丁求古微。
知足知窮知不已,人生著作樂悠歸。

Copyright © 2017 m.haoxunlei.com 湖南政研網 湘ICP備18001534號 版權所有
主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承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辦公室、政策研究事務中心 技術支撐: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