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文明的現代變遷史
——《家山》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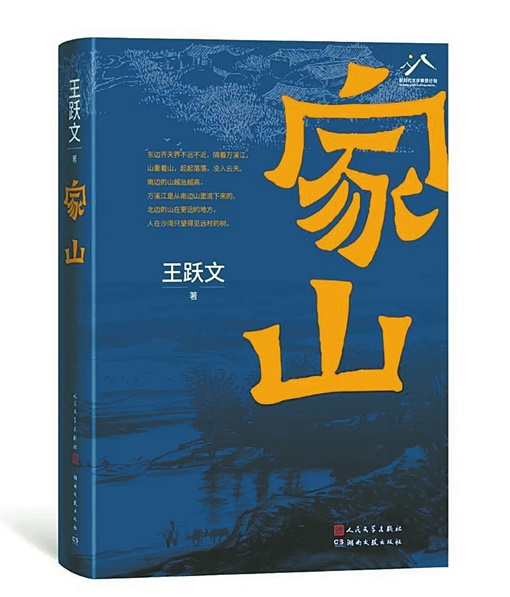
劉啟民
湖南實力派作家王躍文新近發表了長篇小說《家山》。小說名為“家山”,提示著作品盡管寫的是最終將走向革命的現代史,卻立足于耕讀社會的家族世系,帶有鮮明的重視土地、觀照傳統的立場。
作品以一個自然村沙灣村為對象,展現現代歷史上沙灣村里村外不同戶姓和力量之間的沖突與交往,通過沙灣村內倫理、風俗、政治、教育等領域的變動,呈現出中國從耕讀文明走向現代的煌煌歷程。
《家山》最吸引人之處,莫過于對沙灣村中發育生長于此的自然村落格局的精微展現。一個自然村中發端于兩姓始祖的農民家戶,逐漸在中時段的歷史里衍化出了不同的脾性、品質,在經濟關系、社會角色上有了相互牽絆又合作的分工:雇人種田的田家——在過往歷史里被稱之為“地主”的佑德公、遠逸公,以錢財、心力維系著沙灣的安寧與禮教秩序;為人種田的佃家,達公、揚高一家乘著人丁興旺咄咄逼人,在農會這樣的新興機構中試圖立住腳跟;而修根這樣帶有自耕農色彩的農戶,守著自家的土地勤勉耕耘,懷著擴大土地的美夢、絕少參與政事。
村中的婦女群像亦展現出家養、文化的差異秩序來:士家秩序之外的村民桃香,一雙大腳,說話行事豪爽潑辣,反倒能在縣衙門為村里討公道;福太婆、祖婆這樣的士紳之婦,則守著祖宗的老規矩深居家中,成為孩子們走向外界、走向新社會的牽絆;已經在長沙的中學讀過書的少女貞一,則成為自覺改造本土風俗、帶領婦女走向社會治理的新興力量……小說里還寫到慧凈師父為村中人安撫心靈、齊岳為人們敲梆打更、知根老爺齊樹為村里記文錄事。
這些村中相互支撐、合作,但又必然有著沖突的力量,連同著已經被沙灣村村民們講述為神話的先祖創業史,讓讀者意識到,沙灣村儼然就是一個依托于血緣與地緣,在經濟、風俗、政教、信仰多個層面自養自足的小共同體。
小說以沙灣村與外村械斗、又以佑德公以血緣關系巧妙化解為開頭,是別具意味的,它暗示著,一個在傳統農耕文明上生長起來的自然村落,它內在的運轉邏輯。
而沙灣又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現代的洪流之中,還掙扎于宗族血性械斗的沙灣村,早已進入一個更大的故事,參與進更大的歷史進程。文本里的青壯一代齊美、揚卿、齊峰、貞一,他們在長沙、日本接受過現代教育,源源不斷地為沙灣引入了新的現代事務、風俗。無論是齊美、齊峰將沙灣的青壯們帶入了現代軍事訓練班中,還是揚卿的現代水利規劃和新式學堂,抑或是尚屬少女的貞一以一腔天真要改換沙灣婦女的裹腳習俗,新一代沙灣人都努著勁將平等、現代、獨立的文化,將現代的治理秩序引入沙灣。
小說之所以動人,在于它不僅能從后來者的位置寫出這種新舊之變,它還能站在文明的內部,站在歷史后來者的另一端,站在土地之上那些深深受教、生長于儒禮文化之中的人的立場上,寫出新舊之變里人們復雜的情緒、艱難的抉擇。這種復雜包含著佑德公的無奈、凄涼,一生勉力去維護沙灣的傳統政教秩序,終被兒子、被縣長的言行所信服,逐漸接受傳統即將被時代替代的命運;這種復雜也包含著揚卿的無力、心酸,回鄉后揚卿創辦新式學堂,曾教過自己的私塾老師無法融入新式教育體系,勾背離開,揚卿何嘗不感到苦楚;當然,這種復雜更包含著一腔熱血推行新政卻深陷現實泥潭的縣長李明達,離開沙灣的雪夜里刻骨的孤獨,包含了貞一為了解放婦女而奔走,反造成女性新的壓迫時深深的自責……新路與舊路總是好壞善惡交織、問題與希望交互,真正行進在歷史之中的人,往往就是在各種力量、傳統的撕扯之中艱辛的趕路。
中國的現代史該怎么書寫?我們要如何理解曾經發生的新舊鼎革?過去,我們有太多的文本總是站在“新”的一面,站在后來者的位置去言之鑿鑿地寫出這種變革的必然性;有的時候,又全然拋棄這“新”,將推動現代史行進的力量完全依托為“舊”的傳統。《家山》的驚喜之處,在于作者終于褪去了許多情緒化的判斷,它將新舊鼎革的故事收束于土地之上,冷靜地深入到文明的內在肌理,去真正體貼這場文明的變奏,寫出這場變革如何發生、為何發生。它既看到氏族農耕傳統的低效、幼稚甚至荒誕,也看到它的溫存、護佑;既寫出現代規劃的摧枯拉朽,也真實地指出現代允諾的空洞與危機。這正是文明變革來臨時的某種真實。
時過境遷,現代歷史已經走過了百年,五四運動都一百年了,我想,中國人應該更自信地、更自覺地去重新體認新舊鼎革,而《家山》正內懷著這樣的使命與態度。
(《家山》,王躍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Copyright © 2017 m.haoxunlei.com 湖南政研網 湘ICP備18001534號 版權所有
主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承辦單位: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辦公室、政策研究事務中心 技術支撐:紅網